重讀《鼓書藝人》:生計、尊嚴與幸福的難題
原標題:《鼓書藝人》:世界戰爭、中國流民與江湖倫理
摘要:《鼓書藝人》的深入研究須回到“鼓書藝人”這一中國近現代亞文化群體的生存經驗中去。老舍借助方寶慶一家的抗戰流亡歷程、方家各個成員的命運起伏,深刻揭示出北平民間藝人(旗人)在底層討生活的倫理法則:職業技藝只有與家庭倫理之間牢牢綁定才能發揮謀生效能,而世代積累的職業偏見又使得江湖藝人群體不得不面臨道德層面的拷問,無論在社會外部還是家庭內部,從藝的“原罪”都成為揮之不去的陰影。在此意義上,1949年完成的《鼓書藝人》,可視為老舍從國家救亡訴求重新回到個體倫理訴求的象征;身在美國卻講述中國故事的題材選擇,是“中年老舍”結束戰時重慶漂泊、流寓生活的心靈總結;而《鼓書藝人》的失敗結尾,亦預示著1950年后老舍試圖在國家政治的更新換代與個人幸福之間重構小說形式的努力。
關鍵詞:老舍;《鼓書藝人》;流民;戰爭文學;江湖倫理

老舍,1946年,攝于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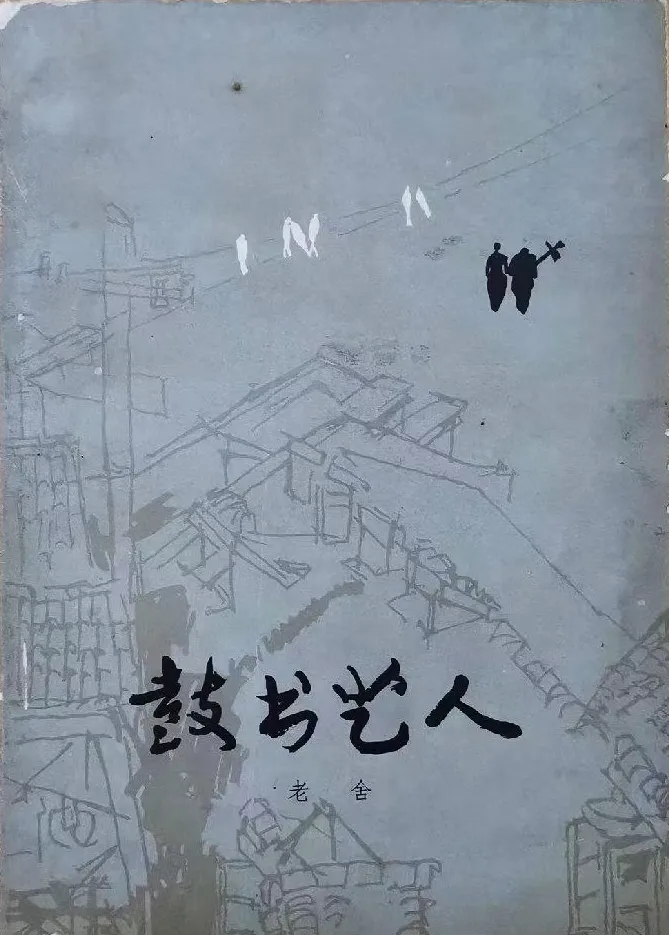
《鼓書藝人》,1982年10月中文初版本

同名電影《鼓書藝人》(1987年),導演田壯壯
《鼓書藝人》是老舍于1948-1949年旅居美國紐約時所寫,英文譯本the Drum Singery由郭鏡秋于1952年翻譯出版,中文原稿遺失,目前《老舍全集》(201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收錄的是由馬小彌復譯的中文版本,最初發表在1980年《收獲》第2期,同年10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單行本。1982年10月,樊駿先生撰寫的《從<鼓書藝人>看老舍創作的發展》一文,可謂新時期第一篇認識到《鼓書藝人》價值與意義的文章,高度評價了作為“杰出的現實主義作家”老舍,按照生活的本來面貌反映城市底層社會的創作特色,并將小說人物方寶慶與秀蓮的反階級壓迫和社會歧視視為民主主義覺悟的代表,進而將這部寫于共和國前夕的作品視為老舍革命思想愈發成熟的象征。新時期之初為經典老作家“翻案”與“正名”的文章并不鮮見,之后對《鼓書藝人》的研究在延續這一敘述話語的同時,似乎尚未找到更有力的言說方式。
重新翻開《鼓書藝人》,幾十年的埋沒外加輾轉的復譯,并未褪去它的光澤,反而那些靜默的歲月為其沉淀出新的魅力,如今讀來依然具有一種濃郁的“老舍風”。小說敘述了鼓書藝人方寶慶一家從北平南下,經濟南、上海、南京、漢口一路逃亡到重慶的故事,1938年夏到1945年秋七年的重慶生活與老舍本人所經歷的時段基本一致。我們在老舍的戰時散文或自述中,很少讀到他對平民/流民群體流寓重慶的深層表達,更多是附著于“文協”這一同業群體的觀照,與此相補充的是:鼓書藝人屬于中國近現代社會的一個亞文化群體,老舍并未徹底將他們推向抗戰的序列,而是趁著戰后相對自由的寫作空間與創作心態,繪制出一幅相對“自然主義”的生存世相。也許《鼓書藝人》會成為這樣一個切片:抗戰時期的北京民間藝人(旗人)如何與重慶地方發生勾連?在舊藝人與新時代的磨合中,人物的命運寄寓了現代中國人的何種困境?作家老舍對江湖者流命運的關照與同時期主流抗戰敘事(《四世同堂》等)又呈現出怎樣的疏離?從作品的細節出發,也許可以將一代戰爭流亡人的經驗與記憶植入時代的肌理之中。
“罪”與江湖藝人的生計問題
中國近現代小說序列中的“藝人”題材不在少數,例如田漢《名優之死》、趙樹理《李有才板話》、吳祖光《風雪夜歸人》、秦瘦鷗《秋海棠》、張恨水《啼笑姻緣》等,但老舍恰逢其時地把《鼓書藝人》置于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歷史事件——抗日戰爭中去,具體環境下具體人物的生活再次展開,讓主人公在戰爭日常生活的洪流中重現真身,似乎有意接續戰前的寫實主義創作風格。或者從時段上來說,“小說家”老舍終于可以靜下心來,操作自己最拿手的小說體式,借助鮮活而切身的流亡經驗鋪展一部新的平民小說。
小說中方寶慶這一人物自有原型,為現代鼓書藝術家富少舫,藝名山藥旦,北京人,滿族。先師從張云舫,學唱滑稽大鼓,早年活躍于濟南、南京、武漢等地,除了演唱傳統的曲目外,更以歌唱時事、社會見聞所長,常以“潮流大鼓”、“時事大鼓”吸引觀眾,創作、演出都具有創新精神。抗戰爆發后,他率班從武漢沿江經萬縣等地入川,邊演邊行,于1938年春節后抵達重慶,與老舍相識,并尊為良師益友。老舍曾多次同友人陽翰笙、田漢、蕭亦五等人去富家,切磋文藝,互相砥礪,使富少舫及其班社演員參加了抗敵協會,并多次參與抗日宣傳義演活動,成為曲藝界一支活躍的抗日力量。老舍小說《鼓書藝人》及1950年后的話劇《方珍珠》均是從富少舫一家的生活與遭遇中取材。
小說開頭寫道“一九三八年夏,漢口戰局吃緊”“一只名叫‘民生’的白色小江輪,滿載著難民,正沿江而上,開往重慶”寥寥幾筆勾勒出1938年中國軍隊戰場失利后的退卻,逃難的眾人無暇欣賞長江兩岸的山水風光而陷入生活的煩惱與無情中。接著,方寶慶出場,展示出極為醒目的識別度,讀者對他的好感也是源自這一人物獨特的經歷。江湖藝人方寶慶,“靠一面大鼓,一副鼓板和一把三弦”,唱大鼓、說評書,走南闖北,養活全家,為人熱情活絡,上船不到幾個鐘頭就認得了幾乎所有同船的人,行事像個伙計,甚至和船長成了朋友,老舍寫道,
“他像個十歲的孩子那樣單純、天真、淘氣,而又真誠。他要是吐一下舌頭,歪一下肩膀,做個怪臉,或者像傻瓜一樣放聲大笑,那可不是做戲,也不是裝假。這都叫人信得過。他是為了讓自己高興,才那么干。他的做作和真誠就像打好的生雞蛋一樣,渾然溶為一體,分不清哪是蛋黃,哪是蛋清。”
方寶慶的出場并未流露出多么濃郁的苦難色彩,反而輕松詼諧,自帶一股“京味兒”。
直到方寶慶上岸后,老舍才觸及到這一人物最為關心的事——說書生意。小說從頭至尾,無論是外部戰爭還是家庭內部事件的爆發,經營說書生意都是方寶慶考慮的第一要務,因為這關系到一家子的吃飯問題。一上岸,“他打開箱子,拿出他最體面的綢大褂,一雙干凈襪子,一雙厚底兒緞子鞋,和一把檀香木的折扇。不論天多么熱,他也得穿得整整齊齊,到城里轉悠一圈,拜訪地面上的要人。他得去打聽打聽,找個戲園子。”想到養女秀蓮,“他必得好好看著她,一步也不能放松。他嘆了口氣。只有秀蓮不出事兒,他才能發展他的事業。”一聽說秀蓮要跟張文走,“他想到他的生意,全完了。秀蓮唱的那一場,誰能頂得了?琴珠嫁了人,也走了!他想起來,他跟小劉可以來段相聲,這也許是個辦法”。書場第一次被炸毀時,寶慶先去看唐家尤其是小劉——重慶獨一份兒能談三弦的琴師。轟炸過后,寶慶到南溫泉的第一件事也是去鎮上看看能不能作藝。好不容易等到抗戰結束,他想,“總得活下去。很快就可以和戰前一樣生活,從北平到南京,愛到哪兒到哪兒,哪兒有人愛聽大鼓,就到哪兒去。是呀,還得上路。賣藝能掙錢,不管花開花落,唱你的就是了。不管是和平,還是打仗,賣你的藝,就有錢可掙。賣藝倒也能寬寬裕裕過日子”。
對于方寶慶來說,生存現實主義成為第一位的信仰。老舍在小說前半部分多次展現方寶慶的活絡:甲板上、澡堂子、茶館、酒館、飯莊,總之“寶慶見人就交朋友”。方寶慶不屑于寄身在茶館甚至茶棚里賣唱,“他是個從北平來的體面的藝人。他在上海、南京、漢口這些大城市里都唱過。他必得自己弄個幛子。他得有一套拿的出手的什樣雜耍,得有倆相聲演員,變戲法的,說口技的。不論哪一樁,他都得去主角”。寶慶算是藝人群體中的“能人”,本身的演藝技能與人際組織能力都較為高明,所以才可以在戰時流動性與摧毀性極大的社會環境中生存。
在這樣的脈絡上,我們便能理解方寶慶為何如此善于交際,他的能說會道其來有自,“多年來跑碼頭,使他掌握了一整套討巧省力的本事”。江湖上所稱道的“金批掛彩”:“金”是相面、算卦;“批”是說唱;“彩”是變戲法;“掛”是賣藝。俗話說:“金皮掛彩,全憑說話。”口才直接決定了生意的好壞。江湖中人除了職業技藝有所區別外,無論賣貨還是賣藝都要仗著能說會道,形成一套獨家“生意口”。賣貨則更是介于賣貨與行騙之間,靠著流利的生意口和手彩蒙混主顧。“走江湖”意味著走南闖北、到處流浪,點出了流民居無定所的浪跡特征。在小說中,作家常常無意識中提及方寶慶的“前史”,讓他回憶過去的闖蕩經歷,“他想起來在北京、天津、上海那些地方,他在散場后跟她一路走回家時的快樂情景”。在重慶開鑼的第一天,“門簾臺帳上都繡著他的名字。每一幅畫,每幅帳子,都使他回想起過去的一段歷史,他到過上海、南京等許多大城市,有過不少莫逆之交。”寶慶且有自己的職業理想,“攢錢辦藝校,收學生,教學生。”雖然戰爭的流動性與摧毀性在這部小說中占據了很大篇幅,但方寶慶一家在重慶八年中除了被大轟炸所折磨,并未常常流露出像大后方知識分子那樣濃郁的“鄉愁”,因為這些流民本沒有固定的“故鄉”可以皈依,他們必須靠著浪跡江湖謀生糊口。
當然,老舍還是給寶慶設置了“從北平來的”這一身份,從事京韻大鼓。京韻大鼓本是發源于前清河間府所屬各縣,俗稱“西河大鼓”,說一陣、唱一陣,“他們走在路上,有一種特別標識,大鼓塞在鈔祃里,搭在肩頭,弦子的鼓子朝上,倒扛在肩上,內行一望即知是走江湖的大鼓藝人”。西河大鼓傳到北京又經當地人加以調整,便成了京韻大鼓。江湖者流中的底層說唱藝人并無固定的作藝場所,基本靠著趕廟會、串街巷、進城市才能勉強維持,有時甚至需要和妓女唱曲兒混在一起輪流表演。因此,這一職業的“下賤”被一般民眾所不齒,像方寶慶這樣有點身份的藝人都對自己所從事的行當常常貶斥:“一輩子作藝,三輩子遭罪”,“即在江湖內,都是苦命人”。可見,鼓書藝人群體的心態逐漸形成一種世代傳襲的卑微色彩與悲觀調子。大哥窩囊廢首先看不起唱大鼓這一門賤業,“他也會彈三弦。但他不愿給兄弟和侄女兒彈弦子,因為干這個傍角的活兒的更低下一等……他向來看不起錢,拿彈彈唱唱去賣錢!丟人!”初入藝場的秀蓮也曾問寶慶,既然賣唱這么“下賤”,我們為什么不找點別的事做呢?繼戰前小說中對人力車夫、娼妓等群體的描摹后,老舍再次揭開了城市底層社會的又一陰暗角落,并將之放在一個更為寬廣縱深的歷史背景中,直接點出這一江湖行當不為人知的一面。這份說書生意的背后是說書這一職業被外界歧視的隱痛。《鼓書藝人》涉及作藝這門自古被視為“賤業”的行當,除了用不多的篇幅描寫方家父女說唱抗戰大鼓,亦收獲了一份抗戰榮譽的短暫興奮外,方寶慶一家對身份的自卑自始至終都未有質的改變,生計難題以及尊嚴難題時時刻刻縈繞在方寶慶一家人的腦中。
“愛”與底層娜拉的“出走-回家”
自1918年《新青年》刊出“易卜生專號”以來,中國版“娜拉”可謂在現代小說中出現頻次最高的人物類型之一,尤其在“五四”文學中占去大半舞臺,魯迅的《傷逝》、茅盾的《蝕》三部曲、凌叔華的《酒后》等,雖然結局有喜有悲,但至少為現代女性提供了出走的勇氣與體驗。但有趣的是,20世紀40年代身處戰爭語境的中國娜拉們是要離家還是回家?《鼓書藝人》從新的視角為我們重寫了戰時中國娜拉出走并回家的故事,集中體現在小說女主人公秀蓮身上,那么,老舍是有意延續五四時期的青年出走敘事傳統,還是借重這一人物譜系另有所圖?
秀蓮的原型為富少舫的女兒富淑媛,藝名富貴花,北京人,滿族。她先后從師程樹棠、白鳳鳴等曲藝名家,學演京韻大鼓,10歲開始正式登臺,經常演出于南京、武漢、鎮江等地,由于年幼而臺風穩重,深得觀眾喜愛,14歲隨父富少舫流落重慶,與老舍相識,演藝也日趨成熟,在做人、作藝等方面均受到老舍的關懷和培養。小說人物秀蓮出場時正是14歲,膽小、活潑、頑皮,還是個孩子,正因為是個女孩,剛好處于少女懷春的脆弱敏感年紀,因此方寶慶時時刻刻存著心事,“她從十一歲起就上臺作藝,給他掙錢。不過他總是怕她會跟那些賣唱的女孩兒們學壞。她越是往大里長,他覺著,這種危險也就越大。于是他也就越來越不放心她。他在娛樂場所賣唱,碰到一些賣唱的女孩兒,她們賣的不光是藝。他有責任保護她,管教她,可不能寵壞了她。為了這,憐愛和擔憂老在他心里打架;他老拿不定主意,到底該怎么做才好。”“他的買賣、他的名聲、他全家的幸福,都和秀蓮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當然她還只有十四歲,什么都不懂。可是她不能老是十四歲,要是她出了什么事兒,他全家都得毀了。”可見,在這樣一個問題重重的家庭中,家長對個人的照顧或成全有賴于個人技藝在家庭生意中的地位。然而從頭到尾,方寶慶和秀蓮都從來沒有正面談過那個最敏感的問題,而是各懷心事。
但是,同行中的琴珠與男人的調笑、游戲刺激了秀蓮對情愛之事的懵懂與疑惑,“為什么琴珠要她跟個男人去逛?愛,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為什么女孩子能憑這個掙錢?”從這些疑惑入手,老舍中途將寫作的重心傾斜到少女秀蓮的愛情之路,先是與小公務員李淵曖昧,后被流氓張文引誘失身,繼而被棄,再次回到方家,最后在生養孩子的過程中重獲新生,身體與精神上經受洗禮。可以說,“鼓書藝人”群體中的方秀蓮這一形象并不比方寶慶遜色,女藝人在這一行當中的性別特征使其處于更為復雜難言的處境。
老舍一開始就小心翼翼地經營著這個女孩的愛情世界,是不安地預感到秀蓮可能會被她所身處的環境毀滅,耐人尋味的是,作家又有意設置了方二奶奶這一并不討喜的角色,在文本中時時刻刻預言著養女的結局,“命中注定,誰也跑不了”。“你逃不了你的命。俗話說,既在江湖內,都是苦命人。命里注定的,逃不了。”哪怕是知識分子孟良試圖以啟蒙的姿態前來說服,她依然言道,“我見過世面。她命中注定,要賣藝,還要賣身。她骨頭縫兒里都下賤。您覺著我沒心肝。好吧。我告訴您,我的心跟您的心一樣,也是肉長的,不過我的眼睛比您的尖。我知道她逃不過命——所有賣唱的姑娘都一樣。”“二奶奶覺著,既然秀蓮是個唱大鼓的,那就決不能成個好女人。二奶奶這樣想,因為她早年見慣了賣唱的姑娘們。”買賣姑娘在這個行當被視為天經地義的事,完全是一種肉身交易,并不算缺德,反而是姑娘們的一條活路。唐四奶奶更是直言道,“干我們這一行的,誰能清白得了。”出身的錨定似乎成為一個必將遭受的“原罪”,時刻提醒著秀蓮的結局——她的“過去”是清晰的,世世代代受制于千年來對戲子的文學想象及其男性狂想。當然,秀蓮并沒有“娜拉”出走的能力,更不可能成為像茅盾《蝕》三部曲中的新女性,她唯一的本錢只有一個女人的身體,而身體的買賣交易便是方二奶奶對這一行當中女性的最大鄙夷。
現實中的老舍可以為富家編寫鼓詞,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孟良也適時出現幫襯方家從事抗戰文藝,成為秀蓮崇仰的人物,但卻無法解答這個少女最關心最苦惱的精神/心理困惑,“孟先生,什么是愛?”“我想知道,有沒有人能愛干我們這一行的姑娘。”關于愛情婚姻的苦悶,孟良完全給不出有效的答案,“他就知道談天說地,對她切身的問題卻不放在心上。秀蓮要替大鳳出氣,找孟良想辦法,孟良一聲不吭,反問道“你說,中國人現在都在干什么?”然后開始長篇演講,從國家抗戰講到女性解放,將秀蓮的命運改變托付于將來的婦女解放,同時將婦女解放的任務與抗戰建國的目標掛靠在一起,顯得生硬唐突。最后給秀蓮安排了“新生活”——“你應該上學去,跟新青年一起生活,一起學習”,白天讀書,晚上作藝,以后作“新中國的婦女”“新時代的新婦女”。
于是,秀蓮的受教育問題在小說中成為濃墨重彩的一筆,剛入學卻因“賣唱”“婊子”“戲子”的身份標簽被同學趕出學校,想當“女學生”而不能的結局直接將她推向墮落的深淵,再次“回到那滿是娼妓、小老婆和骯臟金錢的世界里去”。她理解了琴珠的墮落無非是苦中作樂,大鳳的結婚也是比作藝更好的出路,內心出現一種聲音,“秀蓮,往下滑,走琴珠和大鳳的路吧。這條路不濟,可你也就這么一條路了。快滑下來,別那么不自量了。”孟良在家教她讀書識字,但秀蓮只要想到自己的職業是個唱大鼓的,這些一下子就變得毫無意義。于是,她從學校走向了電影院,“影院里黑乎乎,誰也看不見我,也能明白不少事,跟在學校一樣。”美國好萊塢的電影使她開始向往自由的摩登戀愛,她甚至開始主動尋找愛人,“愛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于是變身邪惡的魔鬼與尤物,渴望一種冒險的人生,小公務員李淵成為她這一愛情練習的道具。在被“知識”拒絕后,她自編自導著這一出危險的愛情游戲,這種危險性無非是將青春拿去豪賭。秀蓮是一個渴望走入現代社會的人,渴望走出自己所身處的舊的腐爛的圈層,對未來生活的藍圖別有一番規劃,但在盲目尋路中被流氓張文誘騙并拋棄,可謂一步踩空,步步滑落,最后黯然收場。
養女秀蓮,在小說中始終處于一種“孤獨”的處境,方寶慶作為她的養父潛意識中有部分養她并靠她的企圖,方二奶奶則時時提醒丈夫趕緊將她賣個好價錢。在單一化的藝人小群體中,孤女秀蓮幾乎沒有出路和退路,只能任由命運的無情之手推出去。也就是說,秀蓮其實屬于“不自覺的人”——弱勢群體,少女等待出路,尋找出路,最后卻只能再次回家,“我想當女學生,結果生了個私孩子。想逃出書場,倒又回來了。”秀蓮的私奔表面看類似于五四興起的子女反叛家庭的“進步”邏輯,實則印證了方二奶奶一直以來對其命運的預言,但也正是秀蓮變成她最鄙夷的那類人之后,方二奶奶接受了秀蓮。最終,“女兒們”覺醒了,覺醒的前提一定是以她們自己去親歷人生為基礎,任何來自家長的道理或規勸都無法成為原初的動力。從這一組母親與養女的關系處理上,我們其實可以窺測出老舍對傳統藝人家庭的關注與改造,在肯定其家庭結構基礎上,關心這門生意背后情感的運行,以及在抗戰這一不可回避的公共事件中如何生長出新的家庭情感與關懷。這是老舍在重慶時期的重要觀察。
在中國人的世代生活中,“娜拉”幾乎是所有女孩子成長史中的一個人物原型。甚至可以說,重慶對秀蓮的意義遠遠大于方寶慶。對秀蓮來說,重慶就是一個命運的樞紐,從女孩成為母親,是自身歷史由舊轉新的歷史樞紐。在離開重慶的前一天,秀蓮回到同居小屋黯然神傷,追憶著她自己的重慶七年。這樣的結尾給人一種時光倒流的錯愕感覺,一切都過去了,坑坑洼洼危機四伏的青春終于就此收場。老舍在此避免了俗套的抗戰大團圓的喜劇結局,在完成《四世同堂》這樣的國家敘事后回歸平民寫作經驗,重新開始強調生活的混沌,接續其早期的青年女性描寫,再次牽涉到“女人墮落”這一文學主題,只不過這些“不自覺的女性”從北京流宕到了重慶。
老舍曾說:
“在我的作品中差不多老是把戀愛作為副筆,而把另一些東西擺在正面。這個辦法的好處是把我從三角四角戀愛小說中救出來,它的壞處是使我老不敢放膽寫這個人生最大的問題——兩性間的問題。”
同樣,《鼓書藝人》的顯在主題一定是由方寶慶支撐,但更具有癥候性的問題卻出在養女秀蓮身上。三四十年代的抗戰情懷與全民熱情是值得懷念的,甚至一直延續到當下的歷史重構中,但對個體而言,精神苦悶和茫然無措的一面被忘卻了,老舍及時承擔了這一任務,替秀蓮這類女性勾勒了過去、現在、未來三種時間貫穿的小歷史,重新關照她們的青春與傷痛,也許生活的混沌可能要比生活的理性更接近于藝術的真實。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視野中,《鼓書藝人》重返戰爭年代的流民世俗生活壓倒了前期知識分子的搖旗吶喊,亂世男女的情欲之流將老舍抗戰初期的國家敘述顛倒重來,此刻抗戰的意義在個人的敘事中被抽空。其實,給方家帶來新生的不是抗戰本身,而是在抗戰洪流中哥哥的枉死,大鳳、秀蓮的孕育與被棄,這一系列切己的創痛才使得家庭內部的情感關系漸漸回溫。
老舍在1949:小說結尾與一段寫作史的考察
小說結尾,秀蓮牽著孩子最后看一眼重慶,老舍借此帶讀者重訪自己陪都生活的一處處痕跡。
“在這山城里住了多年,臨走真有些舍不得。她出了門,孩子拉著她的手,在她身邊蹣跚地走著。她知道每一座房子的今昔。她親眼看見原來那些高大美觀的新式樓房,被敵人的炸彈炸成一片瓦礫,在那廢墟上,又搭起了臨時棚子。她痛心地想到,戰爭改變了城市,也改變了她自己。
在山的高處,防空洞張著黑黑的大口,好像風景畫上不小心滴上了一大滴墨水。她在那些洞里消磨過多少日日夜夜!她好像又聞到了那股使人窒息的霉味兒,耳朵里又聽見了炸彈爆炸時彈片橫飛的咝咝聲。是戰爭把人們趕到那種可怕的地方去的,許多人在那里面染上了擺子,或者得了別的病。
她抱起孩子,繼續往前走。街上變了樣子。成千上萬的人打算回下江去,在街上擺開攤子,賣他們帶不走的東西。
……
他們又上路了。小小的汽船上,擠滿了人。一切的一切,都跟七年前一樣。甲板上高高地堆滿了行李,大家擠來擠去,因為找不到安身之處,罵罵咧咧。誰也走不到餐廳里去,所以茶房只好把飯菜端到人們站著的地方。煙囪在甲板上灑滿了煤灰。孩子們哭,老人們怨天尤人。”
故事到這里本應結束,方寶慶一家從重慶坐船下江,回到他們原先的地方。其實老舍在1946年初從重慶直接飛抵上海,準備前去美國,并沒有經歷這一段坐船下江的“故事”,但他借秀蓮的觀看表達了即將歸去的悵惘,可見作家離開重慶的心理并不輕松,早已被戰爭所改造。《鼓書藝人》的結尾明顯是故意延宕到孟良這一角色身上,特意安排方寶慶與孟良在船上的相遇。孟良不僅是小說中的人物,更是作家穿插的一個啟蒙視角,始終保持對方家父女的審視與指導。他以秀蓮為案例開始的“舊中國-新時代”的長篇演說,細致點數了秀蓮的戀愛悲劇與未來出路,將這個女孩的想要的“愛”“幸福”再次寄托在未來中國之上,且以“長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的鼓詞作為結語。不得不說,對于《鼓書藝人》來說,這是一個失敗的結尾,以歷史理性的進步姿態過度擠占了“返鄉”的敘述空間,帶來某種“卒章顯志”的生硬感覺,失卻了它本有的“民間”意味。如果沒有孟良這條線,《鼓書藝人》所呈現的故事會更純凈。
但是從1950年后老舍積極參與到共和國的文化建設中來看,這一段演說恰恰成為一次有益的嘗試,一次試圖在國家政治的更新換代與個人幸福之間重構小說形式的努力。老舍在《鼓書藝人》的結尾探討社會制度與個人幸福的關系,新舊社會的對比中探索“舊人”的出路與個人幸福,家中人如何獲得新生和重生是他所關心的,這一問題必須掛靠在建設“新中國”的愿景之上。這個“新社會”是以戰后中國的現實、中國傳統藝人的生存狀態、抗戰建國的時代任務等為前提的設想。對于親歷抗戰并即將返回北京的1949老舍而言,“新社會”的現實感必須落實在“個人”的生活與命運之上。《鼓書藝人》及《方珍珠》的續寫可能在文學層面回答了老舍回國的原因:如何讓個人獲得幸福?
《鼓書藝人》的故事發生地在戰時重慶,對老舍來說似乎算是遲到的作品。1940年后,關于重慶的書寫才多起來,文學中的重慶形象也豐富了起來。在《一九四一年文學趨向的展望》中,老舍寫到用舊文藝形式宣傳抗戰的過渡期已經過去了,“大家對于戰時生活更習慣了,對于抗戰的一切更清楚了,就自然會放棄那種空洞的宣傳,而因更關切抗戰的緣故,乃更關切文藝。那些宣傳為主、文藝為副的通俗讀品,自然還有它的效用,那么,就由專家和機關去作好了。至于抗戰文藝的主流,便應跟著抗戰的艱苦、生活的困難,而更加深刻,定非幾句空洞的口號標語所能支持的了,我說,抗戰的持久加強了文藝的深度。”1941之后,老舍便很少借助通俗文體表現抗戰時代的抗戰人物了,他對前線生活并不熟悉,在“文協”所開展的“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運動中,民間藝人與文壇作家的合作成為很有必要的事,如何讓紙上的文字變得口口傳誦,如何在民眾熟悉的舊曲調中賦予新的時代內容,成為老舍抗戰初期著力追求的創作風格,在今天看來粗糙甚至毫無文學審美性的通俗作品卻是老舍花了大量精力和體力所制成的。那么,在抗戰結束后的1948年,老舍奔赴美國后如何回溯自己的抗戰生涯,如何總結?在1949前后這樣特定年代如何反觀知識分子、作家、民間藝人在抗戰時期的位置與功能?
抗戰結束后,大后方作家對重慶的情感在悄然發生變化。豐子愷住在重慶沙坪壩郊區自建的小屋中,地處荒涼,抗戰結束后他賣掉小屋,“遷居城中去等候歸州”,對于住了三年的小屋毫不留戀,“去屋如棄敝屣”。茅盾的話劇《清明前后》(1945)、郭沫若的小說《地下的笑聲》(1947)均展開對戰時重慶的批判與對國民政府統治的詛咒,走向一種仇恨敘事的邏輯。相比之下,《鼓書藝人》并未導向一種作為戰爭“受害者”的言說,去歸咎于具體的“施害者”(日本侵略者、統治階級、闊人等),老舍已經開始淡化重慶作為戰時國都的身份,小說的整體氛圍不是靠激烈的情緒(抒情)來維持,進入文本內部邏輯的渠道是要通向一個具體的家庭倫理關系的厘清。小說中方寶慶夫妻與秀蓮之間的親子關系問題,關于賣藝女性的身體羞恥問題,大鳳與小劉結合所涉及到的職業倫理問題,小劉與方寶慶之間從“拜把兄弟”到“岳丈女婿”的倫理關系切換(小說中的小劉看似篇幅不多,但因琴師這一職業身份功能而成為寓意非常豐富的一個角色),都在大膽地觸及生存、道德倫理與身體意識的一面,老舍對這一階層的心理弱勢進行了反思與細膩的揣摩。藝人這一行當中的買與賣、善與惡,美與丑的雙重性都包含在其倫理秩序之中。從現實來看,藝人班子的成立似乎與技藝并無直接關系,它的維持要靠身體拴住,兩家人對身體羸弱的琴師小劉的爭奪就是最典型的說明,最終必然導向以家族為核心的倫理規范維持他們的生活與心理,生存技能只有與婚姻家庭結構之間綁定才能維持下去。這便是江湖藝人的相處原則與共存秩序,用方寶慶那句意味深長的話來說,“這就是人生,這就是作藝”。
此時抗日戰爭已經結束,老舍正從戰爭宣傳文藝重新回溯到北平市民小說的路線上來,小說沒有再花大量的篇幅控訴戰爭和激勵民眾抗戰,這已經不是1948年創作小說的目標。《鼓書藝人》的寫作,足以成為我們觀察老舍戰后創作轉變的重要參照,甚至比《四世同堂》還要明顯。老舍是要在民間藝人與戰爭日常生活的關系結構中重新建構“平民主體”,他要讓方寶慶一家經歷戰爭帶來的個人改造與關系重組后回到北平。或者說,同一時期寫作的《鼓書藝人》與《四世同堂》對照來看,《鼓書藝人》在主動偏離國家民族敘事的軌道,讓過于民間化的現實生活重回一種原生態的處境,這一類人的命運是老舍一直在關注的,也是老舍在寫作題材上比較偏愛的一類,或者說一個文學系統。雖然老舍并不是像魯迅、茅盾那樣的理性“社會剖析派”小說家,但他對平民歷史的感覺又驚人地犀利、透徹,對平民心理與世故人情的細膩拿捏又是那么精到。表面上看,知識分子孟良的出場略有啟蒙的意味,也有老舍本人的影子,但鑒于老舍與舊派小說傳統有著藕斷絲連的聯系,他的少年生活經歷和京旗民族身份及其歷史記憶都注定了,他的小說創作會與時代的流行觀念保持著一種貌合神離的歷史聯系。
目前學界及影視界都更為推崇老舍的長篇《四世同堂》,北平平民家庭三代人在淪陷區的苦難與抗戰故事更為切合時代主題,成熟厚重、大氣磅礴,篇幅上又占據極大優勢,結構上有清晰的人物性格設定與人物陣營劃分,是作家1941準備、1943動筆仔細安排的結果。人物都是“自覺的人物”,按照革命歷史理性前進的人,抗戰建國牽動著家庭中每一位成員的行動、思想及最后的結局命運,是作品一以貫之的主題話語,“破家立國”似乎成為《四世同堂》民族國家話語視閾下的唯一闡釋形態。但我們也必須指出的是,人物、故事、主題所構成的長篇幅加持了它本身的能量,但整體安排也呈現出一種公式化。相比之下,《鼓書藝人》這樣的小家庭摹寫,流落到異鄉的江湖兒女的面影與輪廓一步步清晰顯現,老舍前期創作中所固有的“自然主義”寫實風格與悲憫之情漸漸回溫。
1946年春,老舍受美國國務院邀請前去紐約講學,《饑荒》和《鼓書藝人》的寫作都是1948年秋的事情,《饑荒》是為了接續重慶時期開始的《四世同堂》,而《鼓書藝人》則是老舍離開重慶后對這一段流亡經驗的反觀,重慶以另一種形象與“感覺”重新進入了作家的小說世界。這部小說中的重慶意象常常被學者們所關注,如坐滑竿、坐船、躲警報、大轟炸、重慶霧等等,成為老舍重慶經驗的直接證據,方寶慶一家在重慶主城與市郊南溫泉之間的季節性往返,正是老舍自身的寫照。或者說,老舍身在異域創作一部《鼓書藝人》,寫的是重慶故事,更是中國故事。老舍在小說中對重慶的城市格局、地勢氣候、建筑特色、交通工具、物價漲落都進行了描繪敘述,提供了一種隱性的下江人漫游重慶的視野風格,為國外讀者了解戰時陪都移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定的地域經驗,也補足了戰后人們回憶陪都生活的情感需要。同時,《鼓書藝人》的寫作也包含有一種“世界視野”的融入:武漢失守、重慶大轟炸、珍珠港事件、滇緬抗戰等世界戰爭大事件主導著中國小人物的流亡路線,北平、上海、重慶、香港、緬甸等各個城市與國家的地理勾連,共同作為方家眾人流徙生活的“場域”,使得這部小說展示出開闊的世界性。
結語
王本朝先生在《老舍研究·導言》中寫到,“老舍的確是現代中國最偉大的倫理型作家,具有豐厚而深沉的倫理情懷。他的小說敘述了一個個帶有倫理意味的故事,表現了生存需要與倫理意識的復雜關系,探討了傳統與現代、金錢與政治、善惡與生死等倫理問題,散發出精深而純粹的倫理氣息。”在此意義上,1949年完成的《鼓書藝人》可視為老舍從國家救亡訴求重新回到個體倫理的訴求,小說安排方家女兒回家、兒孫繞膝的和諧圖景回到北平,依然是建基在中國傳統倫理秩序上對未來的憧憬。與巴金《寒夜》中關注的小知識分子的“家”不同,戰爭在摧毀著這個小家與小家里的人,而《鼓書藝人》卻呈現出樂觀的一面:戰爭以暴力的方式摧毀著人的身體,卻也使這一家人的關系得以堅固并重獲團圓,家庭氛圍一改從前,個人也在慢慢完善自己的人生。《鼓書藝人》的寫作涉及到我們對“重慶老舍”的重新解讀,可以勾連的命題不止“北京老舍”與“共和國老舍”,更有作為平民一份子之“中年老舍”在外漂泊、流寓、輾轉的復雜心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