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潮”訪談|馬林霄蘿:在詞語重量與時代塵埃之間尋找支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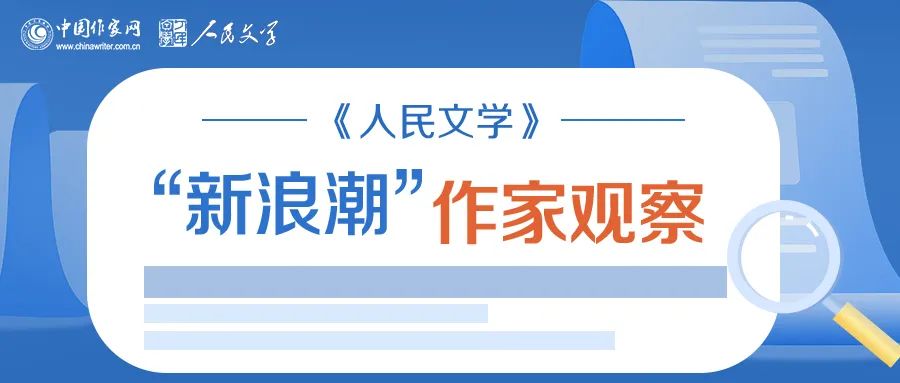
《人民文學》“新浪潮”欄目自開設以來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現已成為雜志的品牌之一。此欄目的作者均系首次在《人民文學》發表作品。今年,中國作家網繼續與《人民文學》雜志共同推出“新浪潮”作家觀察專題,作家訪談和相關視頻在中國作家網網站和各新媒體平臺、《人民文學》雜志各媒體平臺推出。自即日起,我們將陸續推出第三期12位作家:崔君、渡瀾、陳薩日娜、孫孟媛、劉康、周于旸、陳小手、路魆、夏立楠、莊凌、馬林霄蘿、丁甲,敬請關注。

馬林霄蘿,一九九一年生于北京。圖書編輯,寫作者。
在廢墟上種一棵樹
梁豪:馬林你好。記得是2023年5月,在一次幾位朋友的便餐結束后,你跟我聊到手頭正在創作一篇小說,跟北京的澡堂文化有關。我當即起了興致。這興致的其中一層,是我沒料到同代人里會有人關心這個,尤其是你。印象中,你是一個挺潮的人——原來,還能是這種“潮”法。就著懷胎中的小說,彼時我們聊了一些細節,最后我沒忘叮囑,寫好后第一時間給我。這么著,又過了若干時間,有了若干交流后,短篇小說《得高歌處且高歌》發表在了《人民文學》2024年第3期“新浪潮”欄目。一直沒問你為何要寫這樣一篇小說,可以講講它的來龍去脈嗎?
馬林霄蘿:梁豪好!感謝《人民文學》雜志發表拙作,感謝雜志社和中國作家網關心青年作家創作。
我的成長年代和習慣受當代文化影響很深,所以那些被流行文化掩蓋的傳統場所特別吸引我,比如澡堂和茶館。它們看似差不多,命運卻截然不同。現在茶館成了社交新寵,澡堂卻逐漸消失了。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有一個“小傳統”的概念,澡堂文化是城市生活中的民間自發傳統,有著獨特的市井社交邏輯。水霧里浮沉的肉身故事,比任何文獻檔案都更真實動人。現在,刷卡消費取代了手牌,私密淋浴隔斷了人與人的坦誠相見。我們被動接受的變化,或許不僅僅是洗浴方式,而是正在失去某種群體性的記憶。比如澡堂里的白噪聲,拍背聲、象棋落子聲、茶水流注聲……寫這篇小說,是想用文字記錄這些正在被標準化進程抹去的文化記憶。
梁豪:“記錄”的確是小說的天職之一。但小說不同于紀錄片和深度采寫的地方,或許在于它對人著迷卻不介入,它無意于理性和“客觀”的剖解,反倒悉心捕捉并呵護那些心口難開的時刻。比如小說里寫到的宋再來的幾度欲言又止和一聲嘆息。只有文學創作,才能高保真地定格和延宕這份嘆息。作家是始終堅定站在人物這邊的人,同時又幾近透明,他將觀念和情感揉碎在文字里,他把何時摁下快門的糾結與權衡留給自己,而讓描述的對象“是其所是”地活著。
馬林霄蘿:福樓拜教導我們要像上帝一樣隱身,但這種隱身背后往往藏著克制的張力,必須親手碾碎對人物的同情,這種既投入又抽離的矛盾狀態,恰是小說讓人心醉又心痛的根源。現代社會學常談論“不可見勞動”,我想小說的使命正是打撈那些被理性主義剔除的“不可見顫動”。非虛構寫作在追逐真實的路上疾馳,小說家選擇撫摸水泥縫里的野葵。這兩者各有各的了不起。
梁豪:《得高歌處且高歌》是一篇很“拿勁兒”的小說。這股勁兒,指你想要釋放的老北京的滋味和感覺,那種腔調你始終抓得很牢,它成了這篇小說的魂兒。在我看來,有的小說是用來看的,有的是用來聞的,這篇小說最宜“聞味兒”。而當小說里“老北京”跟“新北京”彼此遭遇時,這股勁兒終究有了日薄西山的意味——挽歌再鏗鏘,終歸不免哀涼。“得高歌處且高歌”,縱然有及時行樂的意思,卻也分明是在跟一個行當、一個時代告別,跟屬于自己的崢嶸歲月告別。
馬林霄蘿:或許這就是本雅明說的“靈光的消逝”。在當代中國,新舊碰撞的速度很快,時空的壓縮讓懷舊不再是矯情,而是人們尋找身份認同的重要方式。回遷老人在智能家居旁擺放老式座鐘,這就像數字時代的魔幻現實版馬孔多。文學或許該像艾略特說的那樣,成為情感的客觀對應物,為老澡堂、鴿哨聲找到坐標。這或許就是你感受到的時代挽歌,不是挽歌本身,而是在廢墟上種一棵樹。
梁豪:革故鼎新是宇宙萬物發生發展的必然,不唯人類社會所獨有。“為什么而發展”“如何更好地棲居”,作為后發展國家的我們,身前有很多可資借鑒的例子,不管是正面還是反面的。怎樣在銳意進取的同時,更好地延續從國族到家庭到個體的歷史、文化、生活記憶與痕跡,乃至讓二者相得益彰,值得我們認真思考。面對時代變化,文學的有所作為當然不乏有心栽花的情況,但那些會心的感動與驚喜,很多時候出自無心插柳。而不論有心或無心,“有情”是文學生根發芽壯大的土壤。
馬林霄蘿:文學的“有情”恰在于此:它不負責提供社會發展的標準答案,而是像契訶夫的《櫻桃園》那樣,記下伐木聲,也捕捉月色花影;也像黃錦樹的《雨》,將橡膠林的集體記憶融入半夢半真的氛圍。這種看似“無用”的書寫,反而為瞬息萬變的時代留存了可供回味的精神空間。
駕馭內心的焦慮
梁豪:你生于北京,在這里長大,活成一個一口標準京腔的北京女孩。不管是從歷史文化,還是個體血脈看,北京都可說是你的“父系遺產”。你怎么看待這座北方的大城?
馬林霄蘿:“父系遺產”這個說法或許帶了些文化傳承的刻板印象。父系敘事強調垂直繼承,但北京更像是無數平行時空的疊影。故宮紅墻和798鋼架共存,這種混沌的包容性,恰恰消解了傳統父權體系的權威感。
老舍筆下的茶館掌柜與王朔小說里的胡同青年共享一套生存智慧:他們都在用市井的狡黠對抗著權力的規訓。齊美爾說現代城市是陌生人社會,但北京人總能用兩斤冬儲大白菜打破這種疏離。這種既世俗又超然的特質,讓城市記憶超越了簡單的血脈傳遞。
這座城市教會我最重要的事,是永遠不要試圖用單一概念定義它。它可以是《帝京景物略》里嚴謹的禮制秩序,也可以是《北上》中流動的異鄉敘事。如果非要談遺產,那應該是它容納矛盾、融合對立的獨特能力。
梁豪:時下新北京書寫頗為熱門,在“京味”和“京派”之間,北京敘事還有別的可能性嗎?
馬林霄蘿:老舍筆下的北平是板板正正的,連鴿哨聲都像有固定的飛行路線;而今天的北京記憶卻像流動的水,形態各異。北京的格局也不再是傳統那種層層環繞、以某個中心點向外擴展的模式,而是變成了一種“懸浮層”結構,各種元素交織、疊加,卻又保持著相對的獨立性。
比如徐則臣在《北京西郊故事集》里描繪的城鄉結合部,既是城市不斷向外拓展過程中形成的過渡地帶,也承載著無數異鄉人命運的起伏與轉折。項飆曾提到,“附近”的消失讓人們對身邊事物的感知變得遲鈍,因此在敘事時更需要關注那些容易被忽視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細節。而北京最值得挖掘的素材,或許就藏在那些不顯眼的角落里。
北京敘事的新方向,不是簡單地重復過去或者刻意與傳統對立,而是去探索那些正在發生的、鮮活的故事。當把這座城市的金屬質感、文化交融和人性溫暖同時納入視野時,新的城市書寫就會像星座一樣,每個故事都是一顆星星,既獨自閃耀,又彼此映照。
梁豪:順著你的思考我想到,面對此時此刻的北京,抑或是上海、東京、巴黎,恰恰是怎么寫都可以,前提是有感而發、有話可說,而且會寫,說得精彩。這就回歸到了一個作家的本質。真正的作家,最大的身份和位置焦慮應該在,我的每一次現身,是否都配得上“作家”二字。
馬林霄蘿:這種自我審視或許正是作家的使命。每一代寫作者的共同難題,并不是外部世界允許多少創作自由,而在于如何駕馭內心的焦慮。真正的創作自由類似于西西弗斯的寓言:盡管巨石必然滾落,但推石上山的過程本身即是抗爭。這種矛盾正是寫作的本質:既需要外科醫生般的冷靜,又要承受熾熱情感的沖擊。
當代作家的困境可能比普魯斯特時代更加復雜。當社交媒體賦予每個人表達權時,“會寫”的標準正在瓦解。真正的創作需要在這種混亂中重建價值坐標。作家的身份焦慮不應成為表面的裝飾,而是持續地自我修正。寫作者一生都在調校內心的平衡,在詞語重量與時代塵埃之間尋找支點。
梁豪:你是復旦大學MFA創意寫作專業碩士,一般人聽了,估計跟我有類似的感受,“不明覺厲”。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專業及其相關的學習內容嗎?你正式刊發的第一篇小說,好像就是經由畢業作品修改而成的。
馬林霄蘿:是個有趣的矛盾體。周一下午可能還在圖書館用文藝理論拆解伊斯梅爾·卡達萊,周三上午就要直面王安憶老師的靈魂拷問:“你這段暴雨場景是抒情還是偷懶?”這種冰火兩重天的體驗就像蝴蝶與手術刀,既要保持藝術直覺,又要操練文本解剖的技法。這打破了我對“作家”的浪漫想象。在《2001:太空漫游》中,阿瑟·克拉克說:“每一個現在活著的人,身后都站著三十個鬼。”我們的訓練就是學會在無數幽靈版本中捕捉那個最具生命力的敘事。
梁豪:魯迅“大專”肄業,僅有礦務鐵路學堂的準中專文憑,拋開年少時在三味書屋的舊學教育,跟“文學”基本沾不上邊。沈從文更是只有小學文憑。而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當初進的是圣彼得堡的一所軍校,隨即成為一名軍官,與之相似的是美國的塞林格。這類文壇“嗑兒”比比皆是,我在這里點出,當然是不愿神化文學寫作教育,但同時,我認可作家是可以培養的。正如我在某個訪談里說的,“前提是他本已是一位作家,本質先于存在。外部的培養在誘惑,誘他愛上文學,讓他自己一發不可收。之后,培養是自己跟自己玩,或者自己跟自己過不去”。現在我想補充的是,專業教學最大的好處在于,它引來一伙趣味相投的人,大家湊一塊煞有介事地、當真地聊文學,探討何為存在與虛無。這實在太奢侈、太寶貴了。
馬林霄蘿:關于寫作教育,我始終相信一個樸素的道理:作家是自我教育的產物。我反對將創作神秘化或程式化兩種極端。你提到的魯迅、沈從文這些先例,恰恰印證了文學創作從來不是標準化流水線產品。三味書屋的舊學或許比今天某些創意寫作班的課程更接近好的寫作教育。章太炎先生說過,中國文學的精髓在“小學”(文字訓詁),學院派的條框與沙龍式的玄談同樣危險。我認同的“培養”,更像是福樓拜指導莫泊桑時的苛刻,要求年輕作家在街角觀察馬車夫并找出差異,這種淬煉觀察力的方式,本質上是將日常經驗轉化為文學自覺的啟蒙。
活著的時刻,比血緣更珍貴
梁豪:在一篇關于你母親的印象記里,你說“她與廣西的聯系是一種骨頭的聯系,她對廣西的記憶也是骨頭的記憶”。你和廣西那片濡濕的、與中原和京畿相隔萬里的土地又是怎樣一種聯結?它會潛移默化地對你產生影響嗎?
馬林霄蘿:對每個寫作者來說,城市既是母體又是鏡像。就像張愛玲在上海寫香港,在洛杉磯寫上海,地理錯位反而孵育出文學的多重鏡像。
但血脈比理論更吊詭。越是疏離的坐標,越能照見文化基因的顯影。作品是文字和地理的私生子,城市是胎記也是手術臺。全球化時代,作家必須學會在潮間帶保持平衡:既要有描畫肌理的細密筆觸,又要警惕淪為地方志編纂員的危險。在這個過程中,地域氣質不再是簡單的烙印,創作者的使命或許就是在全球化的湯鍋里守住記憶的活水
梁豪:在這篇印象記里,你提到了母親的不茍言笑,在她看來,“笑得太大,六根不守”。于是,她更多地向內求,在心靈的世界里構建屬于自己的廣闊天地,那里另有一番眾聲喧嘩。在文章中你寫道,對母親而言,“沒有寫作的生活總是表面的生活,不是本質的生活,那樣的生活缺乏心靈的空間,浮躁多于寧靜”。平時你們母女倆是怎樣一種相處方式?你們的異同是什么?
馬林霄蘿:年前在文學活動上,有位記者也問過類似的問題。當時沒想好怎么回答,現在有了新的感受:日常生活、活著的時刻,比血緣更珍貴。
波伏瓦在《第二性》里說母親常把女兒當作分身,但我想補充的是,這種分身效應應當止步于鏡面成像的瞬間……我們現在會共享書單,但絕不互相馴化。溫尼科特說的“足夠好的母親”,在我這里演化成了“適時撤退的女兒”。理想的母女關系,大概就是兩棵并肩生長的樹,各自伸展枝椏,共享同一片風聲。
梁豪:我曾說你寫小說是“無可無不可”,這首先是根據創作量的判斷,此外也是基于對你個人的感受。你有隨性和“佛”的一面,但與此同時,你的內核又是無比堅硬的,或者說莊重。你比我認識的絕大多數人都要堅硬和莊重。所謂莊重不體現在穿著打扮甚至日常社交上,它是一種內心的風格,指向人內在的甚至最核心的地帶。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當然,以上都是我的直覺,未必準確。
馬林霄蘿:謝謝!這或許源于一種自我保護機制。面對過于洶涌的生活命題,反而需要保持松弛的外在姿態來維持情緒平衡。內心的堅持可能源于對人性復雜的敬畏。過于強烈的情感表達反而會掩蓋事物的真實面貌。因此在創作中和生活里,我都更傾向于克制,這種謹慎本身就是對生命的尊重。創作者一生都在尋找現實與虛構之間的合適距離,好在這種矛盾并不需要消除。
梁豪:人生不如意事在所難免,那些悲傷、難過的時刻,你一般會做什么?
馬林霄蘿:完成手邊一件很小但平時沒做的事。比如丟掉過期的藥,給冰箱手動除霜,粘掉衣服上的毛,給吱呀作響的門鉸鏈滴潤滑油,把卡在沙發縫里的硬幣掏出來。
梁豪:目前,你是一名圖書編輯。平時更多寫的是評論文章,為我們品評新近推出的文學著作。我讀了一些,要我形容,文質彬彬,是我哪怕將原作放到一旁也愿意多看幾眼的那類文章。你認為好的評論是什么樣子的?它和你的文學創作是什么關系?
馬林霄蘿:是月光與螢火蟲的關系。作家是施魔法的人,評論家是破解魔術的人。創作是混沌中孕育星云的創世沖動,像福克納《喧嘩與騷動》里的意識流般肆意漫溢;而評論需要詹姆斯·伍德在《小說機杼》里展示的那種X光透視,把小說的血肉之軀拆解成敘事骨骼。當馬爾克斯寫下“多年以后”那個經典開頭時,他是被魔幻現實的風暴卷著走的;而評論家需要像地理學家,測繪出這個句子如何改變了整個拉丁美洲文學的地貌。
但過度理性的解剖會殺死文學的精靈。最好的評論應該像既帶著放大鏡觀察文本的毛細血管,又保持詩人般對語言神秘的敬畏;既要有冰山的冷靜,又要保留地下火山的灼熱。這種矛盾的統一正是文學評論最迷人的悖論。
梁豪:你審閱、編發過許多青年的作品,你如何看待如今的青年寫作?在這里,我更想聽聽你對可能存在的問題的看法。
馬林霄蘿:從出版編輯的角度觀察,近年來青年原創面臨的頭部效應困境仍在,而且越來越明顯。我說一組數據:圖書市場前5%的品種貢獻了80%以上的碼洋,超過七成的新書甚至沒有一次曝光機會。導致“沉默的海洋”的因素有很多:數字閱讀和短視頻對讀者注意力的爭奪,出版機構在營銷資源分配上更傾向成熟作家,新人作品因缺乏市場驗證而被邊緣化,等等。但貼近時代情緒、具有共情力的原創作品仍能突圍,比如我責編的小說《斑馬》聚焦生育話題,因精準捕捉女性話題成為暢銷書。
青年原創的難點本質是注意力稀缺時代的價值篩選,出版市場需要青年作家關注現實與時代,呈現大時代下的小敘事,例如通過外賣員視角折射城市化進程,或以女性職場困境探討社會結構變遷等。這類選題兼具文學性與社會價值。第二是作者的可持續性。能持續輸出獨特視角,而非單本爆款,更易在長線競爭中建立認知度,精準捕捉社會情緒的作品依然有生存空間。
好故事永遠稀缺,找到它的路徑正在變得前所未有地復雜而有趣。
梁豪:我們的書太多了,但足夠提神、真正奏效的太少了。我們的眼睛和耳朵根本忙不過來,更別說腦袋。但正如你說的,永遠應該對好作品敞開。今后碰到好樣的作者和作品,請繼續分享給我。
馬林霄蘿:謝謝!愉快的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