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四色筆記建立女性內心秩序 ——多麗絲·萊辛《金色筆記》一席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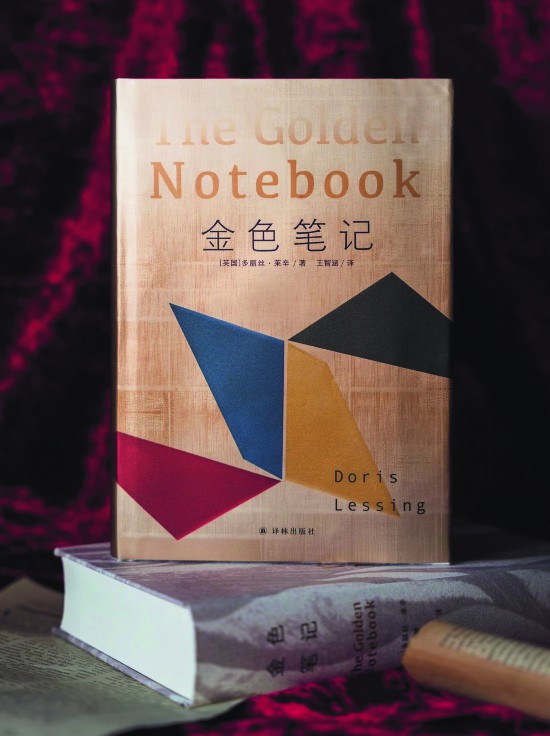
《金色筆記》,【英】多麗絲·萊辛著,譯林出版社,2024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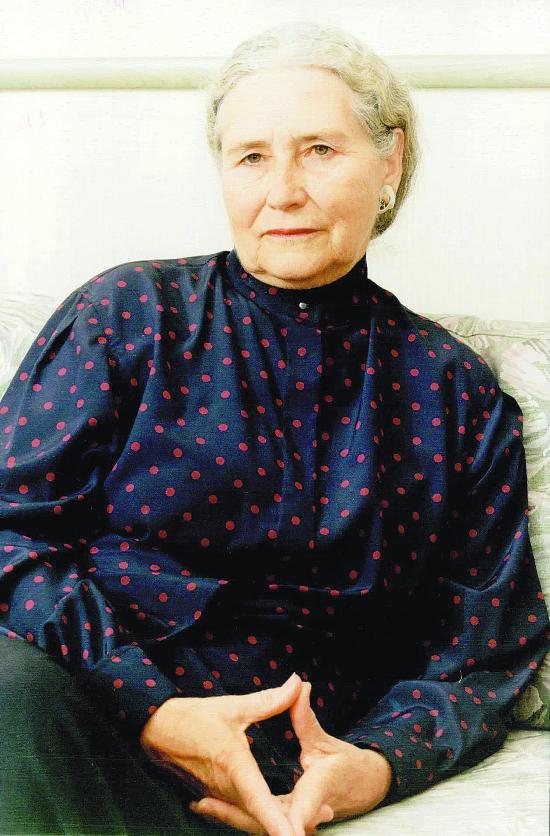
多麗絲·萊辛
近期,在上海市朵云書院戲劇店,新版《金色筆記》譯者王智涵,作家、評論家趙松,文化記者林子人,與現場和收看直播的讀者一起,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多麗絲·萊辛的代表作長篇小說《金色筆記》做了一次深度對談。《金色筆記》的責任編輯王玥主持分享會。
王 玥:多麗絲·萊辛的《金色筆記》中文版已經面世多年,借此次刷新譯本的契機,我們想對這部經典作品發起重讀。在網上一搜索,發現讀者普遍反映此書難懂,還有一位豆瓣網友幽默地說:“讀《金色筆記》不會讓你失望,它會讓你絕望。”所以,我們特別需要再來分享一下《金色筆記》的閱讀竅門,以及一些背景信息,或許可以給大家提供走進它的入口。
趙 松:多麗絲·萊辛的書我閱讀得挺早。英國作家里,我讀的好幾個都是女作家,像艾麗絲·默多克、A.S.拜厄特、安吉拉·卡特,跟她們幾個人比起來,萊辛不太一樣,我覺得她的時代痕跡是很明顯的,換句話說,她屬于生活在兩場戰爭災難之間的那一代人。
讀《金色筆記》,我有一個經驗——不能追求讀得快。它不是一個很高的山,但它的路很曲折,曲折的原因跟它的形式有關。《金色筆記》里的四個筆記本里面,既有獨立的篇章,也有作家安娜對于素材的思考、轉述,還有安娜寫的小說里的人物,等等。小說里套著小說。如果注意力不集中的話,就很容易失去方向。這部小說有很多層次,這種嵌套結構也是作家有意為之。
《金色筆記》里會有很長的一段,不分行,不分段,萊辛想傳達一種氣息,一種氣氛,或者說作家在用這種密集的文字來體現人物的內心狀態。當你熟悉人物和她的潛臺詞的時候,你會有一種代入感,會跟著他們一起去體驗這個過程。
王智涵:我第一次讀萊辛,讀的就是英文版《金色筆記》,我是一邊讀一邊把它翻譯出來的。可能有些譯者的工作方式是把整本書看完,知道大概結構和內容再動筆,而我自己的工作方式是順著小說的脈絡去揣摩、去感受,和讀者一樣。因為提前知道全貌可能就會產生主觀判斷,影響我翻譯時選用的詞匯和表達方式。
我對趙松老師說的“迷路”很有同感。萊辛使人迷路,但她不像詹姆斯·喬伊斯設置大量隱喻讓你猜測,也不像普魯斯特讓你感覺非常絲滑舒適,從瑪德琳蛋糕想到一連串的東西。打比方說,喬伊斯是一個黑洞,一個質量巨大的物體,把人吸過去。普魯斯特像威尼斯水網,但你只要能夠找到一條河流,你就可以坐著貢多拉小船順著水流前進。但萊辛那種跨兩三頁的長段像是一團亂麻,閱讀的第一感受就是混沌、不透氣,像一個人狀態很差的時候,搞不清楚自己腦子里在想什么,但又有一種隱隱的線索纏繞在里面。
上世紀50年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代,西方知識分子普遍在反思西方人是不是得了一種現代病,他們沒有很強的路線自信了。二戰結束,冷戰開始,他們開始內省、自我批判、團體分裂,所以這本書也是分裂的結構。它分成了幾個筆記本,幾個部分之間好像互不通話,一個人的不同側面互不干涉,整體上處于一種分裂、混沌的狀態。
林子人:在《金色筆記》之前,我讀過萊辛的評論集《畫地為牢》,這部作品也已引進到國內。當時萊辛給我留下了強烈的印象,她是一個立場非常鮮明的左翼知識分子,她非常不吝嗇地去分享她對社會的觀點。她確實也是20世紀的各個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
說回《金色筆記》,故事的章節是“自由女性”,主角是一位叫安娜·伍爾夫的女作家和她的閨蜜莫莉,故事從她們與男人和孩子的關系展開。女作家安娜明顯是萊辛以自己為原型的。“自由女性”分成五章,中間又插入安娜不同顏色的筆記本,黑、紅、黃、藍,四色筆記分別記錄了安娜的不同面相、不同身份。最后安娜不再分別寫四本筆記,而是只寫一本金色筆記,象征著她結束了四分五裂的精神狀態,心靈合一。
王 玥:想看故事的話,可以只看黃色筆記部分,它更像是一個傳統的愛情小說。四色筆記在書中是輪流出現的,像是不同主題的撞色,讀者會覺得思路被打斷了。怕混亂的讀者不妨直接從黃色筆記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開始,這樣先一口氣把黃色筆記看完。我猜想,萊辛在寫作的時候可能正在經歷分裂。就像一個人意志崩潰,面對現實沒有頭緒的時候,通過寫來梳理自己,通過文字來盤點自己,四色筆記也是作家在用分類法為自己混沌的內心世界建立秩序。
林子人:萊辛在這本書里面呈現出了女性身份的多元。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習慣把女性和家庭捆綁,比如說她是一個妻子、一個母親,把家庭內的身份作為女性的核心身份。但萊辛通過這本書向我們展示了女性除家庭身份之外,也有很強烈的抱負,她可以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她也可以對這個世界作出非常多的觀察和思考。萊辛在這本書里面向我們展示了女性在公共領域的思考和行動。在今天,這一點對我們的啟示依然非常重要。
王智涵:上世紀50年代是冷戰十分尖銳的時期,美蘇兩極爭霸,美國內部盛行麥卡錫主義,迫害左翼人士,而蘇聯也在高度緊張防范。在兩邊壓力下,英國相對安全,所以書中有很多來倫敦避難的美國左翼人士。倫敦這種大都會成了各國的知識分子聚集、魚龍混雜的地方。現在的倫敦是一個非常精致的城市,消費主義盛行,但在上世紀50年代,倫敦被轟炸得一塌糊涂,經濟非常差,基本上沒有什么娛樂活動,街上還有很多坍塌的房屋,人們需要日夜工作去清理那些瓦礫。書中安娜寫到,她的房子頂上有一個炮彈炸出來的窟窿。那是非常殘酷的景象,所以當時英國社會上,有一種強烈的抱團取暖的心理,左翼知識分子更有一種全球同此涼熱的感覺。我們現在看美蘇爭霸、古巴導彈危機,就是歷史課本里的幾行字。但在當時,時局的變化是讓萊辛這樣的左翼知識分子有著切膚的焦慮感的。
王 玥:萊辛在序言里寫到《金色筆記》被很多人認為是在為女性解放運動吹響號角,但她對此是不認同的。她說:“我當然是站在女性這一邊,但大時代的劇變正在發生,在那之后眼下女性面臨的那些矛盾,自然會煙消云散,顯得‘古色古香’。”萊辛這么說,可能是預測隨著技術的進步,更多的女性走上工作崗位之后,她們在家庭生活里感受到的不平等自然會消失。她認為兩性的矛盾,雖然在人們生活中占比很重,但不是關鍵。《金色筆記》的主線章節叫“自由女性”,自由女性怎么理解?《金色筆記》出版過去60年了,書里描寫的那些女性的困境消失了嗎?
趙 松:不會完全消失,不能把問題剝離出大環境,萊辛表達女性的獨立性,她是在斗爭,她可以作為一個斗爭者展現一種樂觀。人類無論男性女性,面對的不是簡單的一個性別問題,而是一整個社會模式的問題。社會模式可能會讓我們陷入到某種本質的困境里,萊辛描寫那時候的人的掙扎,你會發現當時的人有一些理想化的東西,理想化又總是導致簡單化,很容易變成一種干預社會、干預他人的強烈沖動,最后就變成一種沖突。
林子人:再說回到中國,情況有所不同,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們經歷過一個女性能頂半邊天的時期,我們默認女性和男性一樣都應該參加工作。至少對我們這樣的“80后”“90后”來說,長輩女性出現家庭主婦這種身份比較少,大多都是雙職工家庭。家庭之外,女性當然應該工作,要為社會做貢獻,在家庭內部,家務依舊被默認為女性的職責。我記得上世紀60年代有過一本書叫《李雙雙小傳》,講一個農村婦女成為干部的故事。可見,女性兼顧事業和家庭的問題一直存在并被探討。《金色筆記》里面對這些東西的思考依然有效,從這個角度上來講,今天讀這本書仍然不過時。
王智涵:說到李雙雙這個人物,我想到《金色筆記》里有一小段,寫安娜經常進入冥想狀態,神游天外。她能看到整個地球,有一段寫到她的靈魂飛到了中國,看到一個中國農村婦女在辛勤勞作。安娜不懂她的語言,但是她在對安娜微笑。這段你能感受到一種國際主義的精神,作家是在思考全世界女性的命運。
王 玥:萊辛寫男女關系很直白,好像當年引起不少評議。這種“真人秀式的寫作”,它的文學性在哪里?或者說我們要如何欣賞?
林子人:我讀完“自由女性”第一章節的時候,就立刻覺得它就像文學版的《再見愛人》。兩位女主角安娜和莫莉,談論最多的是莫莉的前夫理查德,他是個大資本家。這個人物角色很像綜藝節目里面的男嘉賓。但是文學作品不一樣,文學作品創造了一個安全距離,讀者不會去把書里的人拿到現實中對號入座。大家會感受到文學所批判的是生活中的某一類人,不是某一個人,是一種原型。讀者不會輕易地去批判誰對誰錯,而是會思考作家在創作這樣的人物、描寫這樣的關系時,想要反映的問題是什么?某種程度上來說,通過文學加工,個人的就變成了公共的東西,這是文學永遠體現它的價值的地方。從這個角度來講,閱讀小說的收獲是再好看的綜藝都沒有辦法取代的。
王智涵:剛剛林老師說綜藝節目跟小說的區別,綜藝節目是要消費觀眾的社交網絡評論,節目設觀察室,希望你代入觀察員的角色,他們跟你一樣“吃瓜”。節目設置觀察員是為了讓你抽離出來,不去共情節目里的人的處境。但是很多的小說,比如《金色筆記》,它會跟你說安娜這個人是怎么想的,她推測周圍人是怎么想的。小說是讓你代入角色,告訴你一個非常真實的處境,讓你隨著主人公的視角去理解世界。這也是小說很難被取代的地方,也是它很珍貴的地方。
(宋晗根據譯林出版社提供的分享會速記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