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馬里亞斯:窮盡一生,用語言揭示語言的陷阱
2022年9月11日,西班牙作家哈維爾·馬里亞斯去世,享年七十歲。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說:“在他這一代,哈維爾·馬里亞斯是最接近諾貝爾文學獎的西班牙作家,這毫無疑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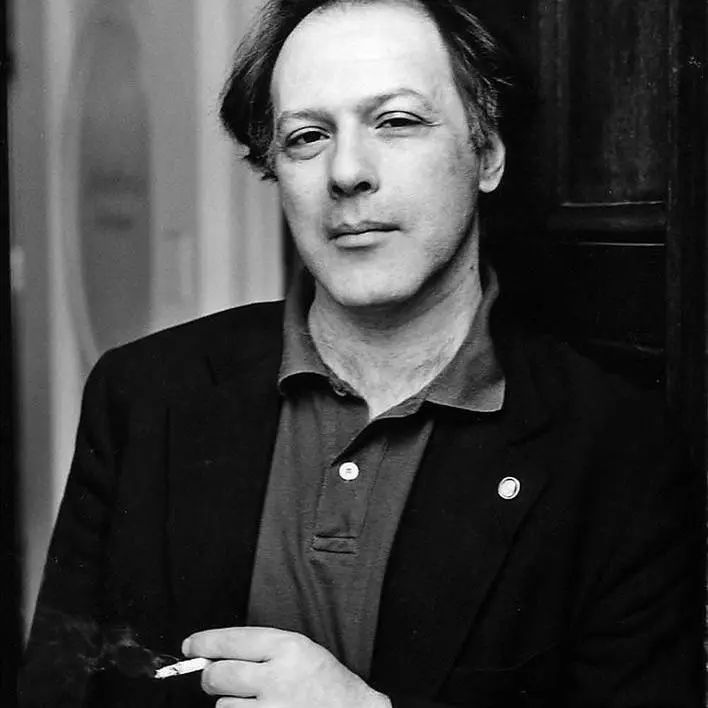
哈維爾·馬里亞斯最知名的身份是小說家,同時,他也翻譯英語經典作品,為導演舅舅撰寫劇本(并且充當群演),十幾年如一日地為《國家報》撰寫專欄,在牛津大學、韋爾斯利女子學院以及母校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授課。去年3月,《托馬斯·內文森》的西班牙語版出版。據他的家人說,他已在打字機上打下了最新小說的幾個句子。
1
哈維爾·馬里亞斯1951年生于馬德里,距離佛朗哥率部下占領首都已過去11個年頭。父親哲學家胡利安·馬里亞斯是奧爾特加-加塞特的信徒,哈維爾尚未出生,胡利安·馬里亞斯就被從前的朋友告發,說他為《真理報》供稿,并與共產黨有來往。胡利安因此坐牢,釋放后仍禁止他在大學教書或為報刊撰寫文章。迫于生計的壓力,他必須尋求國外的教職,先后在波多黎各和美國短暫教書。就在哈維爾出生不到一個月,韋爾斯利女子學院傳來佳音,于是他們舉家遷居美國。在整個1950年代,哈維爾·馬里亞斯都在美國度過,他們住的寓所隔壁,在幾年前住的就是納博科夫。
西班牙巴利亞多利德大學西班牙文學暨文學理論與比較文學系教授巴布羅·紐涅斯·迪亞茲這樣評價父親對哈維爾·馬里亞斯的影響:“不僅僅是道德或政治上的——那是潛移默化的影響,更是對哲學思想、文學和語言的熱情。”哥倫比亞西方自治大學社會傳播學院教授卡塔麗娜·希門內斯·科利亞分析了哈維爾·馬里亞斯在2009年至2013年寫的專欄文章,在238篇專欄文章里,提到了348次他的父親。
1968年,回到西班牙后,哈維爾·馬里亞斯先在有著開明教育理念的“書院”學習,后在康普頓斯大學修讀哲學和文學。巴黎之旅讓他開啟了《狼的領地》的寫作,他住在舅舅、怪杰導演赫蘇斯·弗蘭科的公寓里,白天去法國電影資料館看一部又一部美國好萊塢電影,晚上在香榭麗舍大街賣藝賺錢糊口。是年長二十四歲的西班牙作家胡安·貝內特說服他將這部小說出版。
1970年代,他一邊寫作一邊翻譯英語經典作品。1979年,他翻譯的勞倫斯·斯特恩《項狄傳》獲得西班牙國家翻譯獎。1983年至1985年,他在牛津大學教授西班牙文學和翻譯理論。在半個世紀的寫作生涯里,他出版了十六部長篇小說,寫了數千篇專欄文章,必須一提的是,這些都是用電動打字機完成的,他終生不用電腦。“墨盒越來越難找了,但我并不打算放棄。”
他還喜歡收藏善本書籍,比如初版《項狄傳》,(九卷本,1760年至1768年間陸續出版,其中三本有勞倫斯·斯特恩的簽名。)同時,他也喜歡收藏作家肖像明信片,并且專門撰寫了一篇《完美藝術家》來分析這些肖像明信片:
納博科夫“竟然愿意在照片中露出自己傷痕累累、形狀可怖的雙膝……看起來好像正在抓蝴蝶,襯衫口袋里卻鼓鼓囊囊地塞滿羽毛、眼鏡等物品。顯然,在任何情況下,身上帶著這些東西去抓蝴蝶都是不合適的”;在貝克特的照片中,“鞋子的主人像坐在地板上或縮在一個角落里,仿佛被自己的鞋子給嚇壞了”;威廉·布萊克在假裝自己死了,然而“真正的死人不會像他這樣,那么用力地緊緊閉著眼睛,一看就知道他明明還能睜眼視物,只是故意不睜開而已”。
從一張靜態的明信片就能瞥見大作家的日常行為習慣乃至心理狀態,這種火眼金睛的本事也誕生了一篇絕佳的短篇《血染長矛》,“我”能解開摯友猝死之謎的關鍵,就是那張二人尸體特寫照,妓女的臉、“柔軟而又堅挺的”胸,讓“我”過目不忘,當“尸體”起死回生,坐在餐廳里吃飯時,“我”就有了去質問經辦警察戈麥斯的理由。
2
從第五部作品《多愁善感的人》(1986)開始,馬里亞斯的小說發生了變化:推動小說走下去的不再是戲謔的激情,而是流動的意識。隨著第七部作品《如此蒼白的心》獲得空前的成功(被翻譯成四十余種文字),這個特征愈發清晰,對此,作家也有自述:
敘述者進行一系列的思索和沉思。這種小說形式其實源遠流長,只是如今幾乎被遺忘了,它體現了我所說的文學式思辨。這是一種只發生在文學中的思索方式——只有在你寫小說時才會產生的思索。與哲學思維要求論證沒有邏輯缺陷和矛盾不同,文學式思辨允許你自相矛盾。
也就是說,作家以敘述者的思索(他們在思索各種選擇,同時質疑自己的選擇)顛覆了第一人稱敘述通常擁有的穩定的敘述根基。而另一方面,間隔開一段段思索的,是黑色電影中的經典橋段,比如雨夜路燈下的等待(《如此蒼白的心》)、深夜身穿風衣的殺手進了單身女人的公寓(《貝爾塔·伊思拉》)、倫敦夜總會突然拔出利器刺死人的間諜(《你明日的面孔》)。綿延的思索就發生在行動前,令時間暫停,超負荷地承載平均兩百詞一句的思索。有評論說,就像亨利·詹姆斯在寫一部黑色小說或間諜小說。
《你明日的面孔:毒藥、影子和告別》的開頭和結尾,分別提到獻給父親胡利安·馬里亞斯(2005年去世)和皮特·拉塞爾,后者是牛津大學教授、前特工,在伊比利亞半島歷史方面是研究權威,于2006年去世。但也可以說,《你明日的面孔》是獻給經歷西班牙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那一代人,尤其討論了父輩經歷的道德困境。
3
如哈維爾·馬里亞斯這樣生于西班牙內戰之后,在佛朗哥政權下的開明私立書院接受教育的作家,已不再將文學視作推動社會變革的手段,然而,他無法忽視過去與現在之間的聯系。在巨著《你明日的面孔》之后,馬里亞斯還會寫出《貝爾塔·伊思拉》這樣“一步錯,步步錯,沒有回頭路”的故事。
去年3月出版的《托馬斯·內文森》是《貝爾塔·伊思拉》的姊妹篇,作家討論了一個貫穿歷史的道德困境:殺死某人來懲罰其所犯的罪行,或是預防可能實施的罪行,是否合理?更讓托馬斯覺得困難的,是他們要求他殺死一個女人。
秘密、背叛、謊言、愛的激情與毀滅力,這些永恒的主題在馬里亞斯筆下有了新的詮釋,因為在機器面前,這些詞和它們所代表的意義已像古董一樣遙遠。人的渺小,從他丟失自己的名字開始,這個現實只會越來越嚴峻,馬里亞斯窮盡一生的時間,正是為了用語言揭示語言的陷阱,你可以說他“不夠有西班牙特色”,但他關心的是人類靈魂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