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阿乙:人生只剩寫作
http://www.00444477.com 2016年03月24日10:03 來源:文匯報 周淵 阿乙舊照。(資料照片)
阿乙舊照。(資料照片)  2013年,一場大病突如其來,治療所服用的激素讓阿乙胖了30斤。高遠 攝
2013年,一場大病突如其來,治療所服用的激素讓阿乙胖了30斤。高遠 攝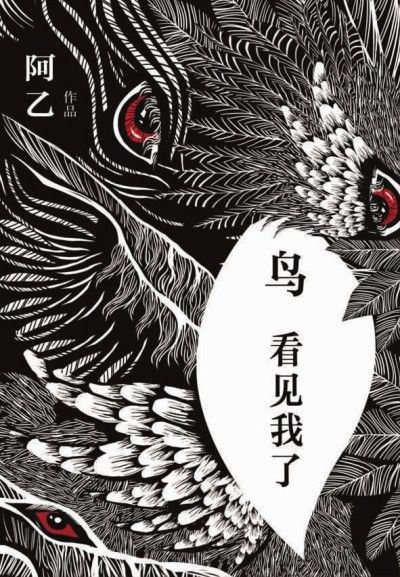 阿乙小說集 《鳥看見我了》。
阿乙小說集 《鳥看見我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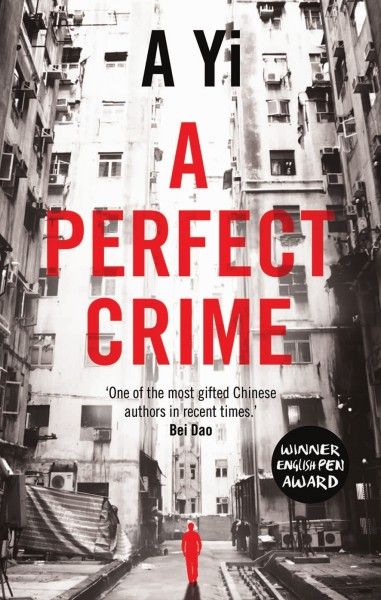 《下面,我該干些什么》 英文版。
《下面,我該干些什么》 英文版。作家阿乙的經歷在“70后”作家中顯得有些特別:從警察、編輯到作家,最終選擇以小說為業,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病又改變了他近乎癲狂的寫作狀態。作家的人生也如同游走在虛構與現實之間,他坦誠地在去年出版的隨筆作品 《陽光猛烈,萬物顯形》 中留下了很多關于生活和寫作的線索,在文學價值之外,這部作品也是通往阿乙內心世界以及領會他的小說意境的秘徑。
近幾年,阿乙不時在聚光燈下收獲鮮花和掌聲,但他的謙卑和對文學的熱愛絲毫未減。談到文學,阿乙說,“我想最終,我是它的仆人”。3月,他的又一本短篇小說集 《情史失蹤者》 即將問世。值此契機,本報記者兩次與阿乙深談,從身世和故鄉、夢境和想象,直到虛構與現實間的思考。
人物小傳
阿乙,原名艾國柱,作家。1976年出生于江西瑞昌,做過警察、體育編輯、文學編輯。曾任 《天南》 文學雙月刊執行主編、鐵葫蘆圖書公司文學主編。
他的作品有小說集 《灰故事》,《鳥看見我了》;隨筆集 《寡人》;小說 《下面,我該干些什么》;自傳小說 《模范青年》;短篇集 《模范青年》 (臺灣寶瓶);小說集 《春天在哪里》 等。
曾獲 《人民文學》 中篇小說獎;鳳凰網年度十大好書獎 (《寡人》);《人民文學》 年度青年作家獎;《南方日報》 中國文學現場2月月度作家;《人民文學》“未來大家TOP20”;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最具潛力新人獎;《聯合文學》20位40歲以下華文作家;《東方早報》 文化中國年度人物;《南方人物周刊》 青年領袖獎;蒲松齡短篇小說獎;林斤瀾短篇小說獎;《小說選刊》 雙年獎;入選中國小說學會年度排行榜。
作家阿乙去年去了美國。一群作家在華爾街參觀,他注意到“一對特別土鱉的男女”,“一看就不是夫妻,男的穿皮鞋、夾公文包,帶著厚重的手機套,風塵仆仆的樣子,我當時就產生了一個幻覺,這就是在洪一鄉的我。如果還在那里,我可能已經當上了中層干部,帶著情人來紐約,男的一路在給女的介紹,就像一個美好世界的導游,但他實際上也是第一次來。他突然停下來說了句,一生一世,只為與你擦肩而過。這話一下子把我驚到了”。
華爾街上恍若隔世的這一幕令阿乙回憶起來倍感唏噓。從警察、編輯到作家,阿乙最終選擇以小說為業。他說,立志去紐約時,正是在那特別土的洪一鄉,“當地沒幾幢房子是二層的,派出所在一棟民居的二層,一層是餐館,沒有柏油路、水泥路,路面上只有泥槽。血氣方剛的年輕人被放在那么一個地方,我那時發誓一定要離開,當時覺得紐約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那么我一定要去那里走一趟。”
阿乙將“逃離”縣城的經驗視為通關,并為自己設定了“省城———沿海———直轄市———首都———紐約”的路線圖,憑著對寫作近乎殉道般的癲狂,一路順風順水地走來。直到2013年,一場大病突如其來,劫后余生,但治療所服用的激素讓這個曾經消瘦的文學青年胖了30斤。即便如此,他也沒有停止對文學的追求和思考。
阿乙對自己的“滿月臉”惆悵而惶恐:“有時候真想大哭一場,但又覺得沒有必要。”一天理發時,他注視著鏡中的胖臉足足有半小時:人何以變成這樣? 變得自己都不認識了。他說自己終生都在焦慮,但多年來仍說不清楚自己是因寫作而焦慮,還是因焦慮而寫作。
寫作、踢球和抽煙曾是阿乙人生的三大樂事,如今唯有寫作一項。紐約書展時,阿乙自嘲不知道哪位“恩公”點名把他拉了進去。“以前想去紐約走一遍,寫一個長篇,這兩個任務都完成了,人生沒什么可后悔的。”阿乙如釋重負。
文學青年的通關之路
他曾是在傳統父權下成長起來的壓抑少年,曾是忍受8年單戀煎熬的小鎮落寞青年,也曾是鄉村派出所郁郁不得志的苦悶警察———這些生活經歷,都成為了日后他寫作中的重要景觀與豐富底色。
1997年,警校畢業的阿乙被分配回瑞昌公安局,兩個月之后,他被分到了更偏遠的洪一鄉派出所,那是一段無處安放的青春。21歲的阿乙某天獨自走過一座山峰,在山頂,他看見遠處綿延的還是山,洼地里生長著和這邊一樣的房子,如果沒有離開,他將和溫柔的姑娘在此生兒育女,生活一輩子……時光暗沉,黑夜像兩只巨臂將要箍向他,他賭氣地發誓,現在就出發,去鎮,去縣,去市,去省城,去沿海,去直轄市,去首都,去紐約。他在腦海中想象著飛機飛過哈德遜河,在紐約的摩天大樓上留下陰影。這一場景與近20年后阿乙第一次去紐約看到的一模一樣:“在紐約,高架橋上車來車往,街道清澈得可以照見人像,飛機的影子像魚兒游過夕陽照射之下的摩天大樓玻璃墻。”他寫下這樣的句子。
阿乙在多部作品中提到同事間一次打麻將排座次的經歷,這幾乎成為了他逃離洪一鄉、逃離本名“艾國柱”的契機:退居二線的老同志坐在北面,主任坐在西面,副主任坐在南面,作為科員他則坐在東面,因為某人手氣不好,大家起身按照順時針方向挪動了一次位置。于是二十多歲的科員坐到三十多歲的副主任座位,三十多的副主任坐到四十多歲的主任座位,四十多歲的主任“退居二線”,坐到了五十多歲老同志的座位。“牙齒變黃,皮肉松弛,頭頂禿掉,一生走盡,從種子到墳墓。”
這段縣城生活的經歷,被阿乙安置在自傳體小說 《模范青年》 中,書中的“模范青年”是他的警校同學周琪源。畢業后,兩人擁有截然不同的命運——周琪源近乎執著地充實自我,學英語、寫論文,想要離開縣城卻又被現實所吞噬,結婚、生子,染上疾病最后郁郁而終;“我”則不顧家里的阻撓,以一種被視為莽撞的姿態出走,成為文字工作者。“如果沒有出來,我可能是不幸的那一個。”阿乙說。
阿乙的首部長篇小說 《下面,我該干些什么》 靈感也來源于警察經歷和社會新聞:19歲的少年在高考前夕殺了美麗、優秀,同時身世可憐的女同學——一個常人心目中的完美寶貝,以此來刺激警察更有力的追捕,制造出一場圍捕自己的行動。
小說的英文版被直譯為 《一場完美的犯罪》 (A Perfect Crime)。《當代世界文學》 雜志的書評人撰文指出,隱藏在血液中的道德之謎涌出,《一場完美的犯罪》 中混合著厭世、逃避現實、媒體怪獸等令人不安的元素。阿乙將視角投射于中國城市化進程和法律變革。一如英國作家安東尼·伯吉斯在 《發條橙》 中營造的抽象且殘酷的世界,阿乙對人性有著更深層次的洞察,青年犯罪動機之豐富令人深感不安。
阿乙則將這種豐富性歸因于警察經驗,這段經歷讓他變得異常敏感。“人對國家機器會有敬畏、恐懼、諂媚等非常復雜的情感,大部分作者只會選取其中之一,但在我的小說里可以看到真實的市民與警察的關系,因為我既當警察又當市民,寫作就是將這些微妙的東西寫出來。”
離開縣城之后,有一次,阿乙夢到自己回到了瑞昌,在縣里謀得職位,親朋們無不關切,贊許他的回歸。他在夢里落下淚來,醒來發現身在北京才安下心來。“無疑是噩夢。”他這樣寫道。
陽光猛烈,萬物顯形
關于那場突如其來的大病,阿乙在《不真實感》 中描繪了一個“陽光猛烈,萬物顯形”的場景:“保安躲在陰暗處。賣煎餅的汗如雨下。高架橋上車水馬龍。你拿著一張CT圖,想到醫生說,肺那里密密麻麻,陰影有點重,我們醫院太小,你去大醫院吧。”那實際上是他的真實寫照。
阿乙將焦慮定為人生中第二檔次的情緒,第一檔次則是當懷疑自己得了肺癌時,檢查持續半年,手術前,阿乙在一只手上寫“別緊張”,另一個手上寫“是又怎樣”,他神經質地反復看著,如同等待判決的犯人,“那時太恐怖了”。
病中的文學青年囈語般的碎片被收錄在去年出版的 《陽光猛烈,萬物顯形》 中。這本隨筆集收錄了從2011年起的156篇文章,約半數是生病的創作。這種緩慢的碎片式寫作是阿乙對卡夫卡式寫作的踐行,“沒有讀卡夫卡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樣去推開文學那扇門。”阿乙曾這樣表示。如今談起這部帶著一道坎似的宿命感的作品,他只輕描淡寫地說:“原先的節奏是一年出一本書,住院導致兩年沒出書,就攢了這樣一部隨筆集。”
對“死亡”,阿乙曾有100種描繪,《陽光猛烈,萬物顯形》 里好幾次提到死亡、遺書、“掉了”這樣的字眼,在一篇名為 《等待》 的短文中,阿乙寫道:“穿著呢子料制服的死神走進來,摘下手套,坐在空蕩蕩的最后一排,一言不發地端詳著他。”
作家坦言,33歲以前他根本沒考慮過死亡。但那一年,60多歲的父親得了重病,母親身體也不好,他突然覺得人生與墓碑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那種摧毀是致命的。”
阿乙擅長自我分析,前一陣他老是懷疑自己要死了,身體的疲憊導致反應遲鈍,不想說話,走在路上覺得隨時會昏厥,令人更加惶恐,他下意識地將這些與死亡掛鉤。“只要疲勞就會有這種感覺:代表死亡的白袍老人就要來了,撒旦如影隨形。我害怕在公眾面前出丑,但內心深處,這種恐懼逐漸加劇。”第一次與阿乙見面,即便是在他自己的家中,與陌生人見面也難掩緊張和戒備。這些都讓人難以與印象中那個意氣風發跨過山和大海,從洪一鄉一路抵達紐約的文學青年掛起鉤來。
在病床上,阿乙讀完了9本 《史記》。病中的種種焦慮,透過紙背清晰地傳遞出來:“每隔一陣子,病人就去領取一點活下去的時間。隊伍排得悶而焦躁。慢慢蠕動、不安的怪獸。”“死亡是最丑陋的事,就像保安在眾目睽睽之下將一個人從舞會抬走。”
至于“劫后余生”,阿乙直言:很慘。大病初愈,他一度覺得自己的身體不能再勝任寫作,但休養不到三個月,“癮又犯了,賊性難改,還是去寫作了。”這回,阿乙規定自己每天寫兩個小時,寫作的工作在上午11點前完成,“相比以前,寫作更有效率,每天寫六七百字或改1000字是最舒服的節奏。抽煙才能寫作、斗酒詩百篇,都是懦弱的借口。”
不是太勤奮,而是太“貪婪”
“體力和以前沒法比,一天只能做一件事。”那次見面,他剛結束了短篇小說集 《情史失蹤者》 中最后一個故事 《對人世的懷念》 的修改,整個人看上去疲憊不堪。他說:“雖然我覺得 (寫作的成就) 是用勤奮換來的,但實際上是貪婪。”
疾病改變了阿乙的身體與容貌,但阿乙對文學的執著卻一如既往。“寫作有時讓人欲罷不能,本來今天早上寫1000字就夠了,但是我太貪心了,一定要把它寫完,結果把一天的良好精力交出去了。”阿乙有些懊惱地說。一雙浮腫的胖手在翻書時或剝龍眼時止不住地輕輕顫抖,那是服用激素的副作用。半晌,他說,你們有幸看到了我恐懼的狀態,要不,喝點酒吧。
對于寫作,阿乙稱自己是運籌帷幄型的選手。他的計劃性很強,打好大綱之后就會按條塊完成。即使是創作那個把他弄病了的長篇 《早上九點叫醒我》 時,盡管焦慮如影隨形,剛住院時他仍計劃帶著電腦到病房去寫作。
在采訪中,阿乙不斷強調自己是個“貪婪”的人,他將寫作的激情和動力總結為“燃燒的文學激情來自持續焦慮帶來的懲罰”。兩次見面,他都不約而同地講到了“猴爪”的恐怖故事,講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從2008年至今出版的每一部作品,我自認沒有哪部是質量很差的,決定出版前我都會細細篩選,寫作付出的代價太沉重了,包括這種恐懼和焦慮,寫作讓人上癮,欲罷不能。”
26歲起阿乙給自己制定讀書計劃,在外國文學的世界里貪婪地汲取養分。癲狂時期,他一天寫作超過20小時,焦慮感也如影隨形,一天只吃一頓飯,用咖啡、煙、酒等等刺激自己的大腦。“貪婪超越了寫作本身,除了寫作其他事情都不管了。我常在想,世界上如果有那么一個地方,大家都在寫作,每人有一個房間,三餐固定,下午有人用機槍命令每個人出來活動,打牌、跑步、做游戲,晚上集體看電影,到9點就熄燈睡覺。我還想發明一種藥丸,人不用吃飯,靠藥丸就能保證營養還不用排泄,剩下的時間都用來寫作和閱讀,還想過做一個自動鍛煉機……現在想來完全是變態,就是人的‘貪婪’所致。”阿乙自嘲地說。
“上帝給了我很多超出‘艾國柱’的東西,當我在興頭上往前趕的時候突然吐血住院,這時才警醒過來。”如今,阿乙“松”了很多。有時他沒來由地覺得自己是“地球上天生的貴族”,“什么都不在乎,也沒什么好羞愧的,我安排自己的生活就是讀書、看好電影,心里對什么都不怵,對金錢和富貴也沒有太大追求。”
(感謝界面新聞“正午故事”記者王琛對本文采訪提供的幫助)
對話
“文學提供一個世界,寫作讓人欲罷不能”
文匯報:你提到過是這本即將出版的長篇小說 《早上九點叫醒我》 把你弄病的,那是一個怎樣的故事?
阿乙:《早上九點叫醒我》 寫的是一位君主死后出葬的故事,小說從一場倉促敷衍的葬禮入手,講述死者如何依靠暴力和詐術對當地進行控制。
寫長篇太孤獨了,有大能者才能勝任,我覺得我還不太行,從2012年一直寫到2013年生病,寫作時備受折磨,寫完只覺得它對不起我,一度不想出版。但現在回頭來看,對它我沒有什么后悔的地方,它或許也是對我過去創作的顛覆。
文匯報:現在還是“全身心充滿焦慮”嗎? 焦慮來自于哪些方面?
阿乙:我這個人終生都感到焦慮,當警察的時候我覺得自己不屬于那里,因為迫切想要離開而充滿焦慮,寫作的焦慮更甚。焦慮成性的人每天都會給自己找很多工作來做,比如我在微博、微信上發了很多讀書筆記,生怕自己不讀書,就下意識地讓自己隨時隨地都保持學習的狀態。這種焦慮還表現在,比如我看電影如果開頭不夠吸引人,可能幾分鐘就換臺了,我迫切地想接受好的東西。
文匯報:你常常否定以前的作品,對于喜歡的作家也常會不斷推翻、質疑和否定,比如你曾提過越來越不喜歡馬爾克斯,這是一種習慣性的反省嗎?
阿乙:讓我保持一種對更好可能性的期待。一開始我對很多作家都很欽佩,之后推翻他們就像躲開暗礁,比如馬爾克斯的 《霍亂時期的愛情》、《百年孤獨》 讓人覺得像大麻,有點嘩眾取寵的味道,海明威、米蘭·昆德拉等也是如此,基本上每位作家都會反思。
有一種說法,一個人談論他所從事的行業越多,可能代表他的創作能力越差,做得好的人往往善于自省。在我看來,文學不是非此即彼,就我的閱讀經驗來說,我只對黑色幽默的作品有點反感。我努力地想把好作品中的營養吸收過來,很多作家還喜歡故弄玄虛擺布讀者,我很反感。
文匯報:從瑞昌縣的警察生活、進入媒體圈、開始寫作,多重身份的轉換會令你感到焦灼嗎?
阿乙:不會,我只會為沒有實現而感到焦慮。比如當警察時會因為沒有成為編輯而焦慮,但當了編輯之后就把警察的生活拋在腦后,每一種新身份都是我想做的事情,就像為了喜歡的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甚至我有段時間跳槽很頻繁,也是在用這種方式換取對自身能力的認可。
文匯報:縣城和警察的經驗一度是你創作的源泉,現在適應大城市的生存狀態了嗎? 這兩種生活分別給你的寫作帶來哪些東西?
阿乙:我覺得我還是洪一鄉出來的那個人,人最開始的十年就決定了他的一生,雖然你老想掙脫它。我覺得北京始終是融不進去的,我也不太愿意融入,它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居住的地方,包容性很強,在這里可以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警察經歷的靈感與始終面對國家機器讓人變得敏感有關。一般寫作者沒有這種概念。在我的小說里可以看到真實的人和警察的關系,從心理上我也想寫好這些。
現在和以前不一樣了,以前老想折騰,現在只要在一個地方寫東西就行,我的欲望很低,也沒什么大追求,已經進入了“老年時代”。(笑)
文匯報:在媒體當編輯的經驗對你的文學創作有什么影響嗎?
阿乙:我當時看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的經典教材 《新聞報道與寫作》 做了很多筆記,寫作的原則大都根據這本書。小說敘事和新聞都講究節奏,但新聞只要快速地把一件事的前因后果交代清楚,文學則要提供一個世界。比如莊園里發生了一起命案,新聞只要把命案講清楚,但文學要描繪整個莊園,里面有哪些植物,有多少女傭、來自什么地方……這和新聞報道的敘事是反的,是慢的。
我看新聞時會下意識地找些寫作線索,比如有個人出車禍死了,別人把尸體拿去當牛肉賣了,這可能是個假新聞,但我可能會寫成鬼鬼怪怪的小說。比如有個農村的老頭吵著要吃牛肉,在農村吃牛肉是件很大的事,附近也沒有人殺牛,賣肉的騎車出去,天下著大雨,路邊有一具尸體,賣肉的一咬牙拿回家把肉剁了,拿到老頭家,卻發現他家大門緊鎖,周圍鄰居說老大爺實在想吃牛肉就自己出門去鎮里買……我想編這樣一個故事。
文匯報:近期還會有哪些作品問世? 未來有何寫作計劃?
阿乙:今年大約要出三本書,馬上要出版 《情史失蹤者》,《早上九點叫醒我》 的意大利版也將會推出。現在壓力沒有那么大,長篇寫完再寫任何東西都很輕松了,我在通過寫短的東西,等待一個合適的長篇小說的機遇。
網友評論
專 題


網上學術論壇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
